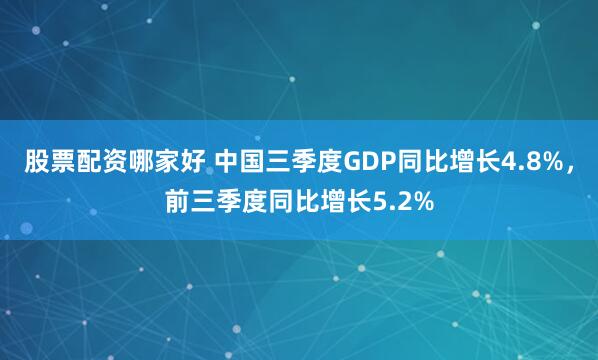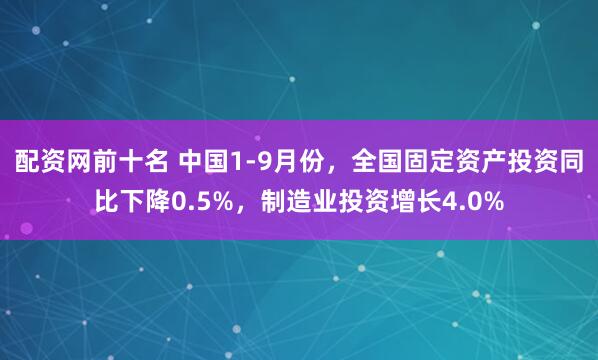美国国债市场的风险与未来
国际货币体系的动摇与重塑
编者按 美国国债市场出现结构性问题——规模持续攀升、流动性下降、波动性加剧……这一系列表现正在侵蚀国际货币体系的信用基础。为此,中国经济时报约请在美国政治、金融领域深耕多年的知名学者,探讨美国国债的结构性危机何在?他们认为,美国国内政策和政治斗争使其国债风险很难化解,且美国也无意从根本上提出解决方案,只是一再地修修补补。美国如上种种很难不让国际社会无助又担心,全球包括中国在内正探寻系统解决方案,进而期望重塑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指出的是,该系列并非盲目唱衰美元霸权,但中国应未雨绸缪,积极寻求体系突围。
核心观点:面对美国国债信用危机以及美元体系动摇,中国亟须构建多层次、系统性的风险防御与体系突围战略,不仅关乎自身的金融安全与经济发展,也将对全球金融秩序的演进产生深远影响。
■陈卫东 初晓
近年来,美国单边主义、霸权思维盛行,美国国债“安全资产”属性裂变,美国国债信用危机已从潜在风险演变为全球金融体系的现实挑战。
美国国内政策加速全球“去美元化”进程
与以往美国国债突破债务上限情形不同,特朗普“对等关税”引发美国国债市场新一轮深度调整,美国国债市场传统优势遭受冲击,流动性风险越发凸显,国债由避险资产转为抛售标的,10年期和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冲破4.5%和5%的年内高位。在美国矛盾交织的政策组合下,美国国债可持续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国力下降与美国国债不断上涨、美元中性利率抬升与巨额国债存量导致财政收支结构失衡、压力加大,引发市场对美国国债偿付能力的担忧。
美国国债被抛售以及信用基础的下调,将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方向转变,加速全球“去美元化”进程,其影响已从市场波动上升至对全球货币格局乃至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塑。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数据,2025年4月美国国际资金出现逆转,净流出142亿美元。其中,外国官方投资人净卖出美国证券173亿美元;外国私人投资人虽净买入31亿美元,但净买入额环比下降2548亿美元。俄乌冲突以来,美元投融资与储备职能遭受反噬,国际债券美元计价份额、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份额分别由2022年三季度的50.2%和60.1%,降至2025年一季度的47.2%和2024年四季度的57.8%。
中国作为持有美国国债的第三大经济体,面对美国国债信用危机以及美元体系动摇,亟须构建多层次、系统性的风险防御与体系突围战略,不仅关乎自身的金融安全与经济发展,也将对全球金融秩序的演进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应完善对外经贸合作关系降低对美依赖
我国可以根据与不同伙伴方的外交关系优化经贸关系定位,因国施策,实现经济合作与政治交往正向循环。
第一,拓展新兴市场,降低出口集中度。对于面临欧美贸易壁垒的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商品,在新兴市场仍具有较大吸引力,未来重点在于加大替代市场的拓展力度。全球南方和金砖国家经济增速较快,增长潜力较大,应成为我国拓展贸易增长点的重要伙伴。非洲经济体与我国双边关系友好、具备较强的经济现代化发展诉求,中资企业可以积极参与这些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助力其构建完善各类经济部门,带动国内中上游产品出口。
第二,推动出口结构转型,提升产品质量,强化我国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能力。强化技术研发,突破高附加值中间品技术壁垒,争取半导体电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中间品发展空间。鼓励面向消费端的产品和服务源源不断“走出去”,将国内消费市场蓬勃涌现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推向国际市场,并根据海外需求进行适配调整,以“国潮”品牌“圈粉”全球消费者,不断构筑新的出口比较优势。
第三,坚持稳定包容的开放政策,不断拓展、深化对外经贸合作安排。探索推进同巴西、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南非等金砖成员和伙伴国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降低美国“排他性条款”对中国开展区域合作的限制程度。深入研究并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加快推进加入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协定,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经贸合作的多元化格局及平衡结构将从根本上为减少对美国市场和美元使用的依赖创造条件。
中国需优化外汇储备结构,渐进式调整美债头寸
第一,策略性减持美国国债。近年来,我国持续减持美国国债,持有规模已从2013年的1.3万亿美元峰值降至2025年4月的7572.5亿美元,减持幅度超过40%,退居持有美国国债第三大经济体。这一战略性调整是应对美国财政状况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必要选择。尽管如此,我国仍面临大量美元风险敞口,部分资金通过第三国渠道持有美国国债,实际持债规模应远高于美国财政部披露的数据。短期来看,美国国债价格下跌直接对我国外汇储备造成估值压力,导致被动缩水风险。美国经济衰退预期升温与美元持续疲软,推高美元资产转换为非美元资产的成本,我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结构调整的操作难度随之增加。美国政府推出的“大而美”法案,将使美国政府债务上限提升至5万亿美元,而该法案将在未来10年使美国国债增加3.3万亿美元。不断膨胀的债务规模持续侵蚀美元信用根基,我国外汇储备面临潜在美国主权债务信用风险,极端情况下不排除技术性违约可能。基于此,我国应密切跟踪美国国债市场的供需结构变化、美联储货币政策与财政部发债联动效应,结合国内经济运行状况,优化外汇储备结构,科学把握美国国债持仓调整的节奏和力度,实现风险控制与收益平衡的双重目标。
第二,优化美元资产投资组合结构。调整持有的美国资产结构。在美联储高利率、高财政赤字等因素推动下,中长期美国国债面临较大价格调整压力,应适度压缩长期美国国债持有比例,增加短期和高流动性产品,以增强应对突发市场波动的灵活性。适度增配优质私人部门资产,将部分美国国债置换为高信用评级企业股权,虽需阶段性承受权益类资产的市场波动风险,但依托企业盈利增长与抗通胀特性,可在较长期限内部分对冲美国国债违约风险。
增加非美资产投资,从战略层面提升外储的抗冲击能力。从区域布局上,根据经贸合作程度,增持经济金融稳定的“友好”国家央行或商业银行存款。与“金砖国家”、东南亚和非洲部分国家联手,扩大联盟内货币当局的货币互换额度。在资产类别上,可以部分外汇储备设立专门基金,参与中资企业在战略资源供给国的资源产业投资运用。以部分外汇储备购置能源、粮食、关键资源和战略性物资,丰富储备资产结构。
第三,完善储备资产管理方式。在满足储备资产安全性和流动性功能的基础上,实施差异化风险考核和投资回报要求,允许具有较高资质的商业性资产管理机构参与储备资产管理,丰富外汇储备的资产组合结构,提高外汇储备安全性及收益性结构的韧性。
第四,战略性考量扩大国内耐心资本来源渠道。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国亟待以国内高效资金循环建设助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考虑到美国正在加大对我国高科技产业风险投资、直接投资资金流入的控制,我国可以以部分外汇储备资金为引导资金,丰富、扩大国内耐心资本来源渠道,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研发、投资,助力国内资金循环体系结构的完善,提高我国资金使用效率。
加强亚洲经济体金融合作,打破“斯蒂格利茨怪圈”的资本循环悖论
第一,建立亚洲经济体资本循环市场。长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通过贸易顺差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再以低收益形式(如购买美国国债)回流美国资本市场,而美国则利用这些资金投资于高回报的新兴市场,形成“穷国补贴富国”的资本循环悖论。我国也被动地参与到这一循环体系中。2024年我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3611.4亿美元。截至2024年末,在我国10.2万亿美元的对外金融资产中,外汇储备资产占比为31.3%,主要构成部分是美国国债。亚洲经济体在全球美元资产外汇储备中占60%以上。亚洲也是吸引全球直接投资最大的区域之一。亚洲经济体深化金融体系合作,建立更加完备的债券市场和直接融资市场,可以形成丰富的外汇储备资金在亚洲区域内的循环体系,从而极大地降低对域外国家市场和资金的依赖。
第二,深化区域金融安全合作。强化东盟与中日韩(10+3)框架下的清迈协议多边化进程,扩大本币互换规模与可用性,提升区域自主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推动建立域内经济体的跨境支付联盟,降低对美元清算体系的依赖。
第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多元国际货币体系重塑。美国主权信用风险产生外溢影响,本质原因是全球跨境收支对美元的依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化解风险的根本方式。短期来看,美元霸权地位难以根本撼动,美元在国际贸易、金融交易等领域的渗透率远超其他货币,形成较强的网络效应和路径依赖。截至2024年四季度,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外汇储备占比仅为19.8%、4.7%、5.8%和2.2%,与美元差距较大。长期来看,美元深陷“特里芬难题”,霸权地位难以持续,当前全球贸易体系重塑、货币体系失序、地缘博弈加剧,或缩短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所需的历史周期,多元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加速演进。未来,人民币有望代表全球南方,与美元、欧元形成三元架构,为国际货币体系注入稳定力量。但值得注意的是,传统货币国际化路径不复存在,如果人民币国际化遵循美元传统路径,将付出巨大成本并面临多重瓶颈,也将受到新的“特里芬难题”制约。因此,人民币需要走出中国特色货币国际化道路。
在完善对外经贸合作关系基础方面,以实体经济发展为依托,推动人民币跨境循环,既有利于夯实双边经贸合作层次,也将创造亚洲区域金融深化合作的重要依托点。基于真实需求,优先区域化发展,丰富周边国家人民币使用场景。大宗商品人民币结算、新能源体系的上下游合作及市场开发,都将开辟人民币环流的新通道,如增加与非洲、拉美等部分国家新能源关键矿产交易,逐步搭建在钴矿、铜矿等领域贸易的人民币应用场景。推动新能源关键矿产的期货期权市场建设,打造具有深度的关键矿产人民币交易市场。
加快数字化、国产化步伐,搭建金融安全网,打造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拓展与周边及友好国家和地区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直接参与者,提升CIPS专线连接范围与系统接入便利性。推进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运营与金融市场业务发展,与主要贸易伙伴联手打造多边数字货币桥,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基础设施。
构建更公正、包容、平衡的国际金融治理新秩序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地缘政治风险的冲击。“美国优先”战略高于国际治理规则,各国被迫在效率与安全间重新权衡,国际秩序更趋碎片化,市场动荡加剧。美国国家利益、霸权取向与全球多元化发展格局相悖。美国通过制度性安排维护其在多边国际体系中的特权,利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票否决权、世界银行的“人事任命特权”,通过干预和影响国际组织制度改革,制衡新兴经济体发展,维护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治理目标来看,西方国家“霸权治理”色彩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公共产品属性相违背。美国通过控制SWIFT-CHIPS支付系统实现金融基础设施垄断,掌握以技术性制裁手段扩展其金融霸权的能力,对不依附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国家和行为施加制度性约束,以此削弱其他国家的金融自主权与政策独立性。
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力量,应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持续推动国际组织结构改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改革议程中,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呼吁调整份额分配机制,提高新兴(300098)经济体投票权比例,推动治理体系改革,破解“美国垄断治理”的制度安排。积极参与全球金融稳定规则的制定与修订,推动形成更公正、包容、平衡,更有利于各国发展的金融治理秩序。
(陈卫东: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初晓: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配资平台投资
配配查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